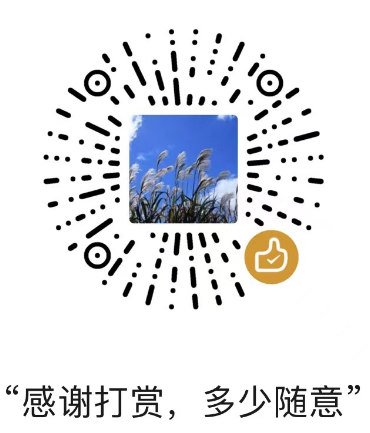斯宾诺莎说过,一个自由的人想得最少的莫过于死亡。
没有必要去多想它,但是有那么多人那样一味回避,丝毫不加考虑,也是不近情理的。
一个人应当对此有个决定性的看法。在死神来到面前之前,谁也不知道自己怕不怕死。
我常常竭力想象,如果有个医生对我说,我患了不治之症,没有多少时候可活,我将是什么样的心情。
我曾经把这心情放进我创作的各种人物的嘴里,不过我知道我这样做时是把这心情戏剧化了,不能说那真是我确确实实感受到的。
我并不认为自己对生命有非常强烈的本能的执著。
我生过好几次重病,但只有一次知道自己是濒临死亡的边缘了;而那时候我已经疲惫得不知恐惧,只想终止挣扎。
死是避免不了的,如何死法也无关宏旨。
有人希望不要知道死亡即将来临,而有幸能够没有痛苦地死去,我认为他们的企求是无可非议的。
我一向惯于生活在未来之中,所以虽然如今我的未来是那么短暂了,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习惯,我的心灵怀着一种特殊的安宁,盼望在不定的年限里完成我刻意制定的人生型式。
有时候我一瞬间是那么激动地迫切冀求死亡,恨不得插翅扑去,有如扑进情人的怀抱。
它给予我的热烈刺激,不亚于当年生活给我感受的。
我陶醉在这种思想之中。在那些时刻,它好像赐予了我最后的绝对自由。
虽然如此,我还是愿意活下去,只要医生能给我保持还可以的健康情况;我欣赏这五光十色的世界,我对它将发生的一切颇感兴趣。
许多和我同时并行前进的人们的结局不断地给我提供思索的粮食,有时给我证实我长年来形成的种种理论。
我将为离别亲友而哀伤。
我不能对某些受我教导和保护的人的命运漠不关心,不过他们依赖了我那么长久,也该享受他们的自由,无论自由将把他们引向何处。
我在这个世界上长时期地占着一个位置,愿意早日空出来让给他人。
归根结蒂,一个人生的型式,关键在于完成。
当再添加些什么反要破坏设计的时候,艺术家便放下了他的作品。
但是现在如果有人问我,这个型式有什么用处或意义,我只能回答说:一点没有。
这仅是我在人生的空虚无聊上面硬加上去的东西,因为我是个小说家。
为了自己乐意,为了自娱,为了满足我一种仿佛是本能的需要,我按照着某种设计,要求我的一生构成一种型式,有开头、有中段、有结尾,一如我拿各处遇到的人们作材料,编写成剧本或者长篇或短篇小说。
我们是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环境的产物。我没有达成我理想的型式,连我比较向往的型式也没有达成,而只是完成了一个似乎还可以的型式。
有许多人生的型式都比我的好。
我相信,我并不仅是受了文人常有的幻想的影响,反正我认为最佳的人生型式属于庄稼人,他耕种、收割,他以他的劳作为乐,以他的闲暇为乐,他恋爱、结婚、生男育女,最后寿终正寝。
我仔细观察了那些有福的土地上的农民们,那里无需过分的劳动而五谷丰登,那里个人的欢乐和辛苦正是人类共同的命运,在那里我似乎看到了尽善尽美地体现了尽善尽美的人生。
在那里,人生好比一篇优美的小说,从开头到结尾循着一条稳定而连贯的线索演进着。